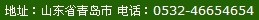|
北京看痤疮好的医院 https://m-mip.39.net/disease/mip_9351241.html 前言 秦汉以降的中国社会逐渐形成了一种优待儒士的传统,在许多历史时段,即使是尚未取得科举功名的基层儒士,也在不同程度上获得了优免权。所谓优免,是指国家依据一定标准豁免部分社会成员的租赋、力役,亦称为复、除等。 进入1世纪,蒙古势力兴起,此前中原等地实行的基层儒士优免制度受到冲击,废坏殆尽。在这种历史背景下,耶律楚材等人推动蒙元统治者实行儒籍制度,部分基层儒士随之获得了优免权。 元明易代后,明代的待士政策与制度又有怎样的推演?前辈学者对元明两代基层儒士优免问题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一些重要成果,对笔者皆有启发意义。但是,此前研究多取或元,或明的断代研究路径,在解说元明易代视野下基层儒士优免制度变迁轨迹及其意义的问题上,则尚有继续探究的空间。 在蒙元入主中原以前,汉地户籍制度虽发达,但并没有设置儒户这一类别,自然也就不涉及儒户优免的问题。蒙元时期创设儒籍制度,起于窝阔台汗时期的戊戌选试。当时,耶律楚材劝导窝阔台任用儒臣,主张开展考选儒士的活动。 蒙哥汗在位期间,听从月合乃建议,亦有考选儒士之举。“岁壬子(),料民丁于中原,凡业儒者试通一经,即不同编户,著为令甲”。忽必烈主政后,在高智耀的推动下,为儒户下发了公文作为免役的凭据。“世祖在潜邸已闻其贤,及即位,召见,又力言儒术有补治道,反覆辩论,辞累千百。帝异其言,铸印授之。命凡免役儒户,皆从之,给公文为左验”。 至元十三年(),元朝最后一次在汉地开展了大规模的儒户考选活动,“国家遣使试儒生于列郡,以经义、词赋两科,中选得为免差儒户”。相对北方儒户的产生过程而言,蒙元在江南地区并未举行专门的考试,而是由民户自报家状,经由官府审验后确定。 南宋儒士陈仁子云:“至元二十六年()二月,钦奉诏旨:‘江南在籍儒人,种田者纳地税,商贩者纳商税,其余横枝儿差役并行蠲免。’九天之云下垂,万木之卉怒长,猗欤休哉,德至渥也。” 至元二十七年(),元朝中央政府在答复浙东道儒学提举司的公函中云:“江南秀才甚多,若尽从供具手状俱作儒户,恐真伪难辨,虚添数多。拟合将归附之初元籍儒户于儒户项下作数,外据已后续收儒户,即今科举未定,合无于民户内抄数。” 年,时在戊戌选试举行之先,窝阔台汗就颁布了《选试儒人免差》诏令,规定儒户享有免除部分徭役的权利,云:“中选儒士,若有种田者,输纳地税;买卖者,出纳商税;开张门面营运者,依行例供出差发除外,其余差发并行蠲免。” 由此可见,儒户除缴纳地税或商税外,其余徭役皆被免除。至元四年(),忽必烈颁布签军诏令,在这道诏令中特别说明免除儒户的军役:“二月,诏遣官签平阳、太原人户为军,除军、站、僧、道、也里可温、答失蛮、儒人等户外,于系官、投下民户、运司户、人匠、打捕鹰房、金银铁冶、丹粉锡碌等,不以是何户计,验酌中户内丁多堪当人户,签军二千人。” 总体来看,蒙元时期的儒户成为国家法定优免对象,且此种权利一直延续至元末。许有壬,延祐二年()进士,卒于至正二十四年(),他认为:“中原至宋播,浙文教几熄,金源氏分裂之余,设科取士,士气奄奄,仅属而吾乡登第者余五十人。圣朝戊戌之试复其家者,子孙于今赖之。” 经实行的僧户、道户免役的制度密切相关,早在成吉思汗时期,僧、道就已经拥有了这项权利。在蒙古统治者优待僧、道的背景下,耶律楚材将儒士比附于已经具有优免权利的僧、道两种户计。 需要注意的是,在蒙古势力南进的早期,汉地与江南地方儒学均遭到严重破坏,当时,儒士群体地位低下,缺乏聚学之所。因此,以户籍制度作为优免儒士的手段,就成为一种既有僧、道户优免成例可循,又可能覆盖更多基层儒士的一种制度选择。 由此可见,元代儒户若家有余丁,必须出丁入学。大德十年(),元政府再次强调此事:“在籍儒人,不遣子弟入学,别习他业,量事轻重,申各处提调官究治。”可以明确的是,原本出身儒户的生员,已经凭借儒户身份拥有优免权。 那么,其他户籍之人为生员者,是否拥有优免权呢?需要说明的是,虽然在忽必烈时期,蒙古统治上层就已经开始推行复建地方儒学的政策,但直到14世纪初,也并未对地方儒学的生员额数做出通行天下的规定。在大德二年(),元成宗诏曰:“学粮赡养师生,天下通例。生员多寡,各随所宜。” 实际上,蒙元时期地方官学的人数,乃至是否实行生员优免制度,各地情况并非齐一。目前,可以从一些地方史志材料中检索出蒙元时期生员具有优免权的事例,如:至大二年(),襄阳路谷城县“择编氓子弟之俊秀者,蠲其庸调,使之就学”。 天历二年(),彰德路“凡诸生隶学者,悉捐杂徭,勿令与凡民等”。至正元年(),汉川县“阅生徒有力役在官者,檄所司弛之”。至正十九年(),绍兴路“诸生之业于兹者,既复其家,俾得遂志于学”。 上述材料时间跨度较大,且涉及多地,由此推测元朝针对生员优免这一问题可能并没有出台内容周详的全国性政令。是否可以对生员采取优免措施,取决于当地官员的态度与经济状况,如汉川县事例:“辛巳(),杨侯观自词臣出宰,政行讼清,百废咸举,将有事于庠宫。 首会廪粟多寡,学籍漫不足稽,则征耕者所授地,约正之得隐田百顷有七十亩,岁增谷一百七十石有奇,曰:‘是足养矣。’”综上所述,从窝阔台汗时期开始,以考选与自报家状两种方式将部分儒士编籍为儒户,并给予儒户优免部分差役的权利。除儒户外,也有一些其他户籍的生员获得了优免权利。 总体来看,蒙元时期以儒籍与生员制度为手段,圈定了基层儒士的优免对象,这一优免制度体系具有如下三个要点:第一,儒籍制度起于年的戊戌选试;第二,蒙元时期的儒籍制度内嵌于户籍制度体系,直接覆盖部分基层民众,形成一种长期存在的基础性优免制度; 第三,蒙元时期并没有就生员优免问题出台通行天下的法规条文,虽然部分生员获得了“复其身”,或者“复其家”的优免权利,但存在显著的地方性差异,缺乏必要的制度保障。 在元末明初战事尚未止息的情况下,朱元璋十分注意对前朝户籍的搜集,并要求诸色户籍人等“各以原报抄籍为定,不许妄行变乱,违者治罪,仍从原籍”。洪武三年(),“籍天下户口,每户给以户帖”。 在明初搜集元代户籍,随后制成户帖的过程中,元代儒籍制度得以传承。正德年间,阁臣李东阳为南京礼部尚书耿裕传世户帖题记云:“礼部尚书青崖耿公以家藏公牍示予,其一为其祖汝明公洪武初所给户帖……户帖称耿氏为儒籍,盖因元之旧而然。”在传世的明代历朝进士履历文献中亦存有许多关于儒籍进士的记载,据钱茂伟统计,明代儒籍进士共有人。 有明一代确有儒户,但明代儒籍制度很快就出现了民籍化的趋向。马志超利用弘治官修的《徽州府志》展开研究,他认为在洪武九年(),徽州府人口统计时将儒户归并于民户,这其实是明代儒户民籍化的滥觞。正统以后,明政府户籍管理松动,儒籍民籍化成为一种常见的现象。 关于明代儒户何以民籍化的原因,高寿仙做过如下讨论:“明初确定户籍,基本上以元朝旧籍为定,保留了一些元朝时期的户籍类别,但明朝本身并不设立此籍。儒籍就是如此,所以洪武年间,儒籍进士特多,其后日益稀少,就是因为在元朝为儒户者才可继续称儒户,而明朝新兴起的儒士并不能归入儒籍。” 高寿仙所论,其实指出了两个重要问题:其一,明代儒户的来源主要为元朝旧籍;其二,明代儒户后继乏人,新兴起的儒士群体并不能归入儒籍。此外,尚存两个问题有待进一步讨论:第一,相对元代而言,明代儒户的规模如何?第二,明代的儒户是否具有优免权?相对元代儒户而言,明代儒户的体量变化趋势如何呢?限于文献记载的缺失,目前很难确切统计元明两代儒户的数量。 萧启庆依据元代浙东道、庆元路、镇江府、松江府、建康路五地数据展开讨论,“五地儒户平均占(五地)总户数的0.85%。元代江南各省入籍户数为一千一百八十四万零八百户,若依上述比例推算,则整个江南儒户总数当在十万零六百四十七户左右,加上汉地儒户(三千八百九十户),总数约为十万四千五百三十七户”。 马志超在统计明代儒户数量时,采取与萧启庆近似的方法,以漳浦县等14个县的数据为依据,推算14个县儒户数与14个县总户数的比例为0.%,以洪武二十四年()全国总户数8445户为准,则洪武二十四年全国约有户儒户。 从萧启庆与马志超二人的推算结果来看,明初全国儒户数远低于元代全国儒户数。但应注意的是,萧启庆明确指出他关于江南儒户数的推算,“仅为一个极为粗略的估计……只可视为最高的可能数”。 综合以上情况来看,其实很难就元明两代儒户数做出确切的说明,于此产生一个可能的推测是:就明初与元代儒户数最高的历史时段比较而言,儒户的规模趋于萎缩,而非扩大。 转载请注明原文网址:http://www.hanchuanzx.com/hcsrk/11364.html |
当前位置: 汉川市 >以史为鉴元明社会管理模式变迁
时间:2023/2/13来源:本站原创作者:佚名
------分隔线----------------------------
- 上一篇文章: 中央气象台喊话湖北你是想霸占榜单前十么
- 下一篇文章: 上游文化丨夜雨丨龚明举彭水之名源于郁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