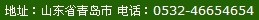|
“我的朋友胡适之”,这是文化古城时期流行于学术、文教界的一句话,正面用这句话和反面用这句话的都有,不过现在知道这句话的人已不多,而且有资格说这句话的人也已渐如凤毛麟角,越来越少,最近听说汪原放老先生也已作古了,这在当年也是有资格称“我的朋友胡适之”的一位。 胡适之先生于抗日战争之后,回到北京(当时称为“北平”)任北京大学校长之职,同时名义上还兼中文系主任,而校务繁忙,自然没有时间兼任,系里的事委托杨振声先生代理,杨先生则又因健康关系,不能到校,实际工作则由唐兰先生负责,唐先生亦于前年病故,三位先生,都是古人了,但他们作为学者的风范则仍留影响于人间。 胡先生当时虽然由驻美大使卸任,出长北大,但仍然是保持着学者的风度,不要看别的,单纯看衣着也可以想见其为人了。一年到头基本上都一件蓝布大褂,冬天罩在皮袍子、棉袍子外面是它,春秋罩在夹袍子外面也是它,夏天除去顶热的时候,穿夏布、杭纺大褂而外,不冷不热的时候,仍是一件单蓝布大褂。北京人把长衫叫作“大褂”,实际还是继承了清朝的叫法。而这蓝布大褂,当年似乎已成了由校长到学生的共同的“制服”了。穿着蓝布大褂,戴着黑边眼镜的校长和穿同样服装的教授、职员在一起,是很难分别出来的。当时他住在东厂胡同,即明代“东厂”的旧址,也曾做过北洋政府大总统黎元洪的府邸。这时由“日本东亚文化协会”接管过来,部分房屋作为北大校长住宅。 他每天坐一部黑色雪佛兰汽车上班,车里总是放许多线装书。到了松公府夹道北大办公处门前下车上班,从未见拿过皮包,而总是抱一大抱书进去,下班回家,仍然是捧着一叠书出来上汽车,天天都是一样的。 有一次十分有趣:中文系开全体会,三位先生都来了,当时是冬天,杨振声先生器宇轩昂,衣服最讲究。散会之后,三位相偕一起出去,由松公府夹道新楼走到前面办公处去,杨先生人较修长,穿着獭皮领、礼服呢中式大衣,戴着獭皮土耳其式的高帽子,嘴中含着烟斗,走在最前面,胡先生身穿棉袍子、蓝布罩衫还夹着杨先生的黑皮包走在后面,唐先生又稍后些,三人边说边走,后面还跟着一大群同学。不知道的人,一定以为杨先生是校长,胡先生顶多不过是个秘书而已。哪儿能从他们的衣着中看出他们的身份和关系呢?于此也可以看出这几位先生的风范了。可能还有不少人记得这些事吧? 最近看台湾远流出版社的《胡适讲演集》第二册,上面有前中央研究院八十一名院士的合影,胡在第一排右数第四人,就是穿着袍子的。合影中大多着西装,只有三四个穿袍子的。张元济先生也在第一排,也身穿袍子,排在中间。 胡适之先生生于一八九〇年十二月十七日,即光绪十六年庚寅。如果现在还活着,那便是九十四岁的老人。现在长寿者多,比他年长的尚大有人在,他是死得比较早一些了。 胡氏安徽绩溪人,胡家是绩溪大族,他父亲胡铁花原在外省做地方官,清代谓之“游宦”;母亲是续弦夫人,过门时只十七岁,比他父亲小三十多岁,只生了他一个,没几年,他父亲就去世了,那时他只虚龄五岁。这是个十分重要的年代,正是“甲午”。其父原官江苏,后改官台湾,在台东、台南做知州。胡氏三四岁时,随父母在台东住过一年多,在台南住过十个月,他到台湾后讲演时自称是半个台湾人,把台东看作第二家乡。甲午之役,清室将台湾割让给日本,中国官吏均撤至厦门,他父亲胡铁花就客死在厦门。 胡氏是他母亲一手教导成人的。人常说严父慈母,而胡母却是集父严母慈于一身,母亲对他管教极严,幼时上学读书,放学回家,进屋门前;先要将一天所读的书背诵一遍,才准进屋吃饭。不然,立在门前重读,甚或跪在门前重读,直到读熟为止。十四岁到上海上学,三年才准许回家一次。胡适一九一O年考取官费留学生,放洋留美,先学农业,后学政治经济,又学文学哲学,最后学成,获得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学位。有名的《文字改良刍议》就是在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时写的,这篇文章打响了新文学运动的第一炮。也奠定了他一生享盛名、做学者、成闻人的基础。以上情况,在其《四十自述》一书中,写得很清楚,我只略作介绍而已。 胡氏后来作驻美大使,是他政治生涯的极限,于此而后,则美人迟暮,大可伤矣。 距今五十四年前,一九三〇年即民国十九年十二月十七日,是他四十岁生日。当时正是北京大学文学院人才济济的时候。那时他家住在景山后街米粮库。北大同仁便在他家为庆四十整寿。用的是东兴楼的席。出面贺寿的人有北平白镇瀛、宁波马廉、东台缪金源、织金丁道衡、湘潭黎锦熙、汉川黄文弼、吴兴钱玄同、唐河徐炳昶、绍兴周作人、北平庄尚严、沧州孙楷第、如皋魏建功。共十二人,都是著名学人,可以说是极一时之盛了。由他的大弟子魏建功撰文,好友钱玄同书写,写了一篇别开生面的白话章回小说体寿文“胡适之寿酒米粮库”。这篇寿文开始引他的《沁园春》“更不伤春,更不悲秋,以此誓诗……”作为引子,后面便说他对新文化的贡献,结束段云:民国十九年(一九三〇)十二月十七日便是他的四十整生日,他的朋友和学生们中间,有几个从事科学考古工作的,有几个从事国语文学研究和文字改革运动的,觉得他这四十岁的纪念简直比所谓“花甲”、“古稀”更可纪念……十九年他再住北平,定居米粮库,便赶上是生日,他从前自己诗里说“幸能勉强不喝酒,未可全断淡巴菰”,是早已受了酒戒了,这次生日应该替他开戒,好比乡下老太婆念佛持斋,逢了喜庆,亲友来给他开了斋好饱餐肉味一样。 如今为了要纪念“人”、“事”、“地”,便写了恁个题目:《胡适之寿酒米粮库》,后面并署名盖章。这篇名文,原件是钱玄同先生法书中的精品,现在则不知是否尚在人间了。至于那十二位贺寿的人,我所知者,似乎只有孙楷第先生硕果仅存,依然健在,其他都已是古人了。 当时还有吴其昌先生祝寿云: “加紧继续,千百世以后的文化运动; 切莫误会,四十岁便过了青年时期。” 抗战初起时因汉奸罪死于非命的黄秋岳氏,当时也曾集辛弃疾词为寿联,共两副,其一是: “刘伶元自有贤妻,宁可停杯强吃饭; 郑贾正应求腐鼠,看来持献可无言。” 另一副是: “扶摇下视,屈贾降旗,闲管兴亡则甚? 岁晚还知,渊明心事,不应诗酒皆非。” 信中说“改天用宣纸写”,写了没有,就不知道了。 作者简介:邓云乡,学名邓云骧(.8.28----.2.9)山西省灵丘东河南镇人。上海红学界元老,与魏绍昌、徐恭时、徐扶明并称上海红学四老。青少年时期,先后在北京西城中学、师范大学和私立中国大学求学。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先后任教山西大同中学,天津中学。新中国成立后,在北京中央燃料工业部工作。年10月起,先后在苏州电校与南京电校教书。年1月在上海电力学院教书,至年退休。 转载请注明原文网址:http://www.hanchuanzx.com/hcsrk/11318.html |
当前位置: 汉川市 >邓云乡胡适之寿酒米粮库
时间:2023/1/27来源:本站原创作者:佚名
------分隔线----------------------------
- 上一篇文章: 动态动机与情绪管理心理情景剧走进
- 下一篇文章: 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