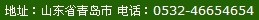|
按:本文为参加年6月在丹江口召开的“汉水文化暨武当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而撰,发表在冯天瑜先生主编的论文集《汉水文化研究》(中国国际广播音像出版社年版p-)上。当年为撰本文,曾采访过张重安、李正荣、李正华诸位先生。其中前二位已于去年远去,特记于此,以表感怀。本文虽写汉水文化,但主要素材来自侏儒山地区。当然,文章写于十多年前,有些观点我已有所改变。但这是另一文章(可写,但也可能无能力写了)的内容。本文就不修改了。另,参加会议的,是李永铭与同事范小方教授,故同时署名。 发源于陕西西南宁祥县蟠冢山的汉水,向东南蜿蜒曲折一千五百多公里,流经陕西南部和湖北西部中部约三十余县,汇入长江。汉水流域近2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水量充盈,自然条件优越,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上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这里大多为纪元前楚国的辖地(楚国疆域曾北到陕西的丹凤)。三国时代大多数威武壮阔的历史剧就在这块土地上上演。历史上这里是兵家必争之地。近代以来,这里经历了太多的战乱。从军参战、自保家园,是历代汉水流域人民无尽的话题。因此,汉水流域既保存着古朴的民风,又有着尚武的传统。早在宋代以前,汉水流域的武当山就出现了不少武林高手。经元末明初张三丰的发展,形成了民间“北少林、南武当”的武学格局。武当内家拳享誉海内外,对汉水流域的武学传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据《襄阳县志》载:“明清时期,封建统治者在襄阳县设有武考场,对县民练武有一定影响。清末民初社会动乱,民众为护庄保村防身自卫,习武练拳盛行。”新出的《汉川县志》据同治《汉川县志》说,清初至同治年间,汉川有武进士12人,武举人55人,武秀才多人。《天门县志》介绍了类似情况,说清道光年间当地有武进士12人,同治年间有武举人2人,武秀才2人;光绪年间有武举人6人,武秀才12人。“清末明初,本县群众体育活动以武术最盛。”民国20年(年),岳口地区有武学47所。《汉阳县志》也记载说:“汉阳县体育活动历史悠久,而武术尤盛。由明至清,县内出武举人、武进士余人。武术在民间较普及,也有以此谋生的。……民国时期,出现民间武术团体。” 在一般情况下,“习武术者多数人是为了健身、防身,有的富户借此晋升武官,有的贫民则是学艺谋生。”然而,在封建宗族势力影响下,尚武之风非常容易走入歧途。 在古代,汉水流域早就有先民在这里生活繁衍。早先,人们挽草为标,划地为界,选择依山傍水、土地肥沃、避风向阳之处,扎下了根。由于这里环境适宜,分散居住不会造成生产生活困难,因此,除交通要道的城市外,农村往往一家一户,居住散乱。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世代繁衍的人口逐渐发展,家族聚居形式慢慢出现。在明清时代江西迁湖广(也有来自其他地区的)过程中,人口增长加快,聚族而居逐渐相沿成习。一个家族共居一地,遵守共同的生产、生活习俗,在社会生活中具有了一定的独立性。其中有一些家族由于人口太多,原有村落无法容纳,自然或人为地分成几支,部分分支迁出原地,另觅新环境发展,形成一个家族前后左右相邻的几个村子(自然也有相隔较远的)。这种村落最明显的标志就是同姓聚居。这种同姓聚居的生活方式,使宗族形态与宗族势力逐渐发展起来。仅汉水下游的汉阳县,在民国时期已建有祠堂、修了族谱等,形成完整宗族形态的就达姓之多。其他无祠堂设施但聚族而居者当不在少数。笔者调查,这一带纯由杂姓组成的村落极少,有的杂姓村中,也有一个主要的大姓,该大姓在村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一般来说,宗族是由男系血缘关系的各个家庭,在宗法观念的规范下组成的社会群体。“大小宗族建祠堂、修族谱、订族规、立族产……宗族宗旨讲的是‘尊祖收族’、‘起孝悌之心’、‘谋族姓之发展’、‘辅官治所不迨’,而实际上发展到以大欺小、以强凌弱、相互械斗。”众多的大姓大族聚集一处,最初还可能和睦相处,久而久之,各种冲突会不时发生。他们的土地连界,祖坟相邻,同在一个集场贸易,共饮一湾河水,本就免不了磕磕碰碰。而有时双方都想占有同一块地,或在集市上占有更大份额,或多使用一些河水灌溉田地,或独霸渡口交通权,甚至小孩们的争执斗口,长期积累,都会使双方成为仇敌。为了宗族自身的利益,甚或为了宗族中某些人或某个人的利益,宗族就会充分运用其掌握的武力向其对手挑衅甚至挑战。一言不合,即约期械斗。学武以自保,按宗族的解释,包括保卫自己的家庭、家族直到宗族,这样,宗族械斗就不可避免地发生了。《汉阳县志》在谈到武术运动的兴起时,就讲到宗族势力在其中的作用,指出:“旧时武术盛行的原因之一是县内人多田少,多外出谋生,而社会长期动乱,需借助武功以自卫。再就是家族聚居,常为柴山湖草相互械斗。有的大姓宗族规定,凡为宗族械斗而死者,在祠堂内立牌位,赡养遗属。还由于寺庙丛林散布各地,有武功的僧道常比武传艺。这些都使县内民风强悍、习武之风盛行。”另外,一些公共活动,由于组织不力,加上以往的各种矛盾纠纷,也会演变出意外。比如这一地区都有五月端午划龙舟的习俗,通常由宗族出面组织这一活动。每一姓组建一龙舟队,各姓之舟以颜色相区别。几姓之舟同在一河道表演,“往往因龙舟竞赛引起械斗”。宗族械斗显然成为这一地区尚武传统的灰色一页。 汉阳县(原县治在现今的武汉市汉阳区之钟家村,20世纪50年代,汉阳区与汉阳县分离。90年代,该县撒县改区,现名蔡甸区)居汉水的末端,汉水在这里入长江,完成其公里的辉煌。而在20世纪的前半叶,汉阳县和与它紧邻的汉川、沔阳等县,在灰色的尚武文化上也具有代表性。 《汉阳县志》对此有一简略说明:清末民初,县内宗族械斗时有发生。多因争柴山湖草、鱼藕之利及天旱抢水而起争端。大族强占、压制弱小;如果势均力敌,就发生械斗;械斗中如有伤亡,就一直打官司。该书还举了下面两个实例。 清宣统三年(年),天大旱,遍地龟裂,汉阳太渡河水几近干涸。周郑二姓抢水灌苗,双方鸣锣聚众,各出动余青壮年,大斗于黄金山下。结果郑姓被杀死2人,伤36人;周姓打赢了也有伤亡。官司打了两年多,周姓中有5人坐牢,2人死于监狱。 民国元年(年)4月,汉阳小查湖李、高二姓为争夺藕湖三汉港发生械斗。李姓族长、族正挑选青壮年名持械驾舟60余条,将高姓所植莲藕捣毁。高姓以逸待劳,用5支土铳半途回击。结果李姓重伤2人,轻伤1人,中铳弹丸者不计其数。官司一直打到年,高姓花去银元0,全摊到族众身上。 汉阳县辖的一个地方,在其所编的资料中谈到宗族械斗问题时也说得很具体:“本地特点,多以一族聚居一村,因之邻村之间或因占有土地扩大族产,或因口角纠纷,往往引起矛盾,小则诉讼不断,大则树旗械斗,为了宗族利益,虽伤亡惨重,亦在所不惜。如郑余二姓为玩龙灯借路、郑周二姓为河滩之争、李刘二姓为上坟走路等大型宗族械斗,影响很大,而小型的宗族诉讼与械斗,则不胜枚举。” 上述材料中,我们至少可以看到,经济利益的争执,是发生宗族械斗的一个主要原因,但不是唯一的原因。口角纠纷、竞技比赛也会引起厮杀。更深沉地思考,这里是否还有人的野性的复苏与挣扎?在中国,英雄时代过早地结束。在等级制度及儒家伦理的高压下,人们压抑自我,以假面具的样式进行人际交往,个性难以得到张扬。一旦出现械斗的场合,人有了宣泄自我的机会,于是慷慨上阵,六亲不认,演绎出多少人间悲歌。 总体上看,在宗族械斗发生的背后,是封建宗族势力的恶性膨胀。事实上,宗族间争议的问题,绝大多数在开始时并不是很大的、不能协调解决的问题。只要双方平心静气,一些问题本就不存在,一些问题完全可以协商解决。或者如果法制严谨,行政管理严格,出现问题沿正常渠道疏导,大多数纠纷都可以消灭在萌芽状态。然而,宗族械斗发生前、进行中,都看不到当时的政权组织在哪里。械斗本身就说明,在宗族看来,问题的解决不能指望官府。因为官府吏治腐败,它不愿意开罪地方宗族势力,也没有这种化解矛盾的能力,只能依靠宗族自己拳头的力量,战胜对手,才能达到目的。我们所看到的是,宗族势力的发展强化了宗族自身的霸气,而在一定意义上,制造矛盾、激化矛盾,正是强化宗族势力的需要,这就造成械斗不断。因此,撇开常见的经济争执,宗族械斗的根本原因在于宗族自身的恶性发展。 一个弱势的宗族是难以挑起家族冲突的,它首先要自保。但也有不顾一切而冒险挑战,通过械斗树立自己本宗族的声望的。强势宗族则大多对外飞扬跋扈,扩大宗族间的利益冲突。俗话说,一山不容二虎。两宗族常常会为他们在当地的“声名”而刀枪相见。汉阳汉川两县间或各自县内都曾发生多起划龙舟争名次,或直接以龙舟颜色为由,发生械斗,使得血洒河滩,河水殷红。民国二十八年(年),汉阳县县西李刘二姓械斗,起因是刘姓清明上坟,故意走李姓村子,并经过(按走大路可以不经该村村中)李姓祠堂。按一般规矩,宗族集体活动经过外姓祠堂时,不得坐轿骑马,以示尊重。否则就是轻视、挑衅。刘姓有备而来,在走过李姓祠堂时,仍坐轿骑马,耀武扬威。李姓人当然不服,当即与之争执起来,并约定下午见阵。当天下午,两姓在附近一山下对阵,双方都集中了族中精锐,武师领头,青壮年随着跟进。一场混战下来,双方多人重伤。械斗结束时有人检查李姓的领头武师李某所使用的木棍(当地称“杆子”),上有各种伤痕多处,足见打斗之激烈。事后人们谈论这场械斗,都不明白二姓血肉拼杀的背后原因。但有一点,大家都看到了二姓武力的威猛。宗族通过械斗,确实显现了其自身的力量与地位, 很明显,频频发生的这种宗族械斗,其影响是不可低估的。 宗族械斗造成严重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如上述周郑两姓的械斗,当场被杀死2人,重伤40多人,监狱中又死2人。为打官司,双方都未少花银两。而对死者、入狱者家属的抚恤,伤者的医治调养,则又不知花费多少。看其他各次械斗,人员财产的损失都是惨重的,有的宗族甚至从此衰败破落,无法重整旗鼓。 宗族械斗造成农村社区长期的矛盾与不和。汉阳县横龙乡的郑、余、周三姓,均为当地大姓,且均聚族而居,各自的村落都很大,人口众多。民国初,三姓分别为太渡河水及河滩等经济利益甚至口角争执,多次发生械斗(前述周郑械斗即其中之一次)。民国二十七年(年)重阳节,郑姓雕刻了一对石狮,立于该村西北方向,分别面对周姓、余姓村子,意为吞舟(周)、吃鱼(余),用以诅咒周余二姓。这一行动,强化了该村与另外两村的矛盾,使得其后多年,郑周、郑余之间的死结无法解开。 宗族械斗使官场腐败更其严重与公开化。宗族械斗之后,接下来的是长期的诉讼。旧时代的诉讼,或称打官司,完全不是依法办事,真正是“衙门八字朝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地方士绅与衙门官府互相勾结,理大不如钱大,这是公开的事实。因此,宗族械斗使官府有了公开敛财的机会。30年代初,汉阳、汉川有一争讼。事起于西湖堤修堤民工的争执。南屏院西湖堤位于汉阳县境内。但这里是汉川南河地区的出水口,因此,这一带堤防与涵闸由汉川县负责组织施工,汉阳汉川以及外地都有一部分农民在此打工。工棚相连的民工因口角导致械斗,外地民工(他们是汉川县雇的外地人)被当地民工打伤了几人,于是伤者到汉川县存案。为了处理此案,汉阳县的国民党清乡团团董、前清秀才万某坐轿来到汉川。他在县衙大堂上指着门外的一口水塘说,谁能用钱填满这口水塘,官司就胜了。对方只是一些出苦力的农民,怎能与他抗衡,只好放弃赔偿。官司不了了之。前面讲到的李刘两姓械斗,官司打了几年,毫无结果。因为两姓都有后台。刘姓有一人在县政府为官,李姓则有一名当地著名乡绅,双方各施解数,包括银两,县府只能让其拖下去。 械斗迫使一些人泯灭了人性。事实上,械斗双方因居住接近,亲戚关系总是相当繁杂的,甚至直系血亲也相当多。对阵时,亲朋好友相遇是无可避免的。按宗族规矩,一旦与外族械斗,凡族中成年男子,任何人不得缺席,否则族规会先进行清理门户。有的宗族为检验某人是否忠于本族,竟有意安排其与自己的亲戚对阵。表兄弟之间、舅甥之间、姑父内侄之间、姨父姨侄之间,乃至翁婿之间,刀枪相逼,血洒当场,几乎每阵都有,造成无数人伦惨剧。汉川旧港张姓与汉阳横山朱姓为一藕湖起争议,张姓杀了朱姓的两个人,并藏尸湖底。朱姓发现后怒极,两姓组织械斗。这一场械斗中,就有翁婿对阵,并造成一死一伤。前述李刘两姓械斗,李姓领头武师李某与刘姓领头武师刘某,是极要好的朋友,相互间极敬重。平时在一起切磋武学,评判乡情;或呼朋引类,酒馆豪饮。但上阵后,两人都不含糊。刘某在这次械斗中身受重伤。尽管事后人们看到他们二人在镇上携手同进酒馆,但隐藏在他们心中的痛苦明眼人是一下就能看出来的。 对参加械斗者造成长期甚至终生的心理压力。上述张朱二姓械斗中,朱姓有两兄弟武功极高,直冲前阵,杀死张姓中最孔武有力的两大汉。此后二朱精神极度紧张,神情恍惚,总想起战场上血淋淋的场景。这年春节清晨,朱家按风俗早起出行(早起敬神开门放鞭炮纳福)。朱氏兄弟一开门,就见张氏二大汉血淋淋站在大门口。两朱二话不说,抄起刀枪出门冲杀,却扑的一跤跌在了门外。两朱于是卧床不起,不久离开人世。世界上本没有鬼,朱氏兄弟的见鬼,无非是他们长期的心理压力造成的幻觉,这就是悲剧之所在。 械斗破坏了生产,影响了地方安宁。每次械斗,从准备到实施直到收拾残局,村民得长期停工,操练演习,甚至农忙也在所不惜;械斗前的挑衅,往往以破坏青苗开始;械斗中的战场,很多都是已耕种的土地;械斗后人员伤残死亡,又哪里顾得上生产。这种械斗的发生,对当地治安安全会产生长久的负面影响,甚至造成社会的动荡不安。 械斗进一步加强了宗族势力。本来,即便是同一家族,其内部由于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差异,总是有着多方面的矛盾的,其中也包含着阶级矛盾。然而,通过宗族械斗,宗族矛盾被放大,其他矛盾都被弱化了,甚至被淡忘了。胜者宗族势力自然被强化,败者宗族要复仇,更要加强宗族建设。经过械斗,个体家庭增加了对宗族的依赖性,宗族也就更加巩固了它在农民中的权威。 总之,宗族械斗给社会留下的是一个沉重的话题,给汉水文化蒙上层层阴影,加载了灰色的页码。 年全国解放后,封建宗族势力遭到毁灭性打击,但是它并没有彻底退出历史舞台。尽管它已不可能像上半个世纪那样猖獗,可宗族械斗仍有发生。特别是最近20年来,宗族势力卷土重来,修谱建祠之风绵延不断,确实有些让人担心。尚武以健身,对振奋精神、提高自信心,无疑是有作用的。人的潜在的野性与英雄主义发挥得当,对于国家民族的振兴,无疑也是有意义的。但是,必须加强引导,不能放任自流,特别是不能让新的宗族势力与之结合。今天,弘扬汉水文化中具有现时代意义的内容,抛弃汉水文化中灰色愚昧的东西,应该引起我们的强烈,并作为建设新时代精神文明的重要环节。愿宗族械斗永远成为历史。 李永铭,侏儒山夹榜湾(现属高墩村)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儿时住侏儒山老街,年大水后搬到老家。汉阳十二中毕业后,回农村务农。在大队民办小学(含初中)先后工作5年,修补地球足足8年。年入湖北财经学院(原湖北大学、今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哲学专业,毕业后留校任教。先后主要从事逻辑学、历史学等教学工作。曾入南开大学研习逻辑学。除本科各专业外,曾任中共党史、中国近现代史、专门史(台湾史)、逻辑学研究生导师,并担任逻辑学导师组组长。学术兼职主要有:湖北省逻辑学会秘书长、湖北省历史学会理事、湖北省社会科学联合会委员、湖北省逻辑与语言研究会副秘书长、中国逻辑学会经济逻辑专业委员会委员等。主要著作是:逻辑引论、法律逻辑学教程、法律逻辑学导论、经济活动中的逻辑、批判性思维:以论证逻辑为工具、中国当代政治思想史、中华开放史、台海问题与统一之路、:武汉大会战、桂系三雄: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43位战犯的后半生等。退休后住侏儒山正街。 范小方,湖北天门城关人,年兰州大学历史系毕业,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中国近现代史教研室主任。担任中共党史、近现代史、专门史(台湾史)研究生导师,并任后二导师组组长到退休。是湖北省历史学会常务理事兼副秘书长。主要著作有:国共两党关系史、国共两党谈判通史、国民党理论家戴季陶、蒋家天下陈家党、二陈与CC等。 李永铭范小方赞赏 人赞赏 长按向我转账 受苹果公司新规定影响,iOS版的赞赏功能被关闭,可通过转账支持。 小孩白癜风能治好么救助贫困白癜风患者转载请注明原文网址:http://www.hanchuanzx.com/hcsmj/1439.html |
当前位置: 汉川市 >宗族械斗汉水文化中灰色的一页以20
时间:2018/3/3来源:本站原创作者:佚名
------分隔线----------------------------
- 上一篇文章: 汉川分公司我与汉川共成长主题征文活动
- 下一篇文章: 乐活我的汉川春节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