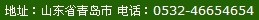|
治疗白癜风医院哪家好 http://yyk.39.net/bj/zhuanke/89ac7.html 时间回到年10月3日,武汉市第一中学举办80周年校庆。曾庆瑞作为武汉市第一中学毕业55周年的校友,受邀出席了武汉市第一中学80周年校庆; 曾庆瑞是中国传媒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广播电视文学系创系主任。他长期致力于学术研究,涉及汉语言学、中国现当代文学、电视剧等诸多领域,是国内首个电视剧高等教育完整体系的建设者之一,为创建中国电视剧艺术学学科体系做出卓越贡献。年被评为“北京市高等学校教学名师”,年被授予“中国传媒大学突出贡献教授”称号。 曾庆瑞为一中的校友们讲课 曾庆瑞为一中的校友们讲课 武汉一中是我成长的文化大摇篮(上) 作者:曾庆瑞 年2月,我考进了济生小学高小部,读小学五年级。那时候的中、小学都是春、秋两季招生。后来,年我考进武汉一中也是二月入学。直到年夏天,武汉中小学招生改变办法,原先的春、秋两季招生合并为每年秋季一季招生,我提前半年算初中毕业,于年9月继续考取了武汉一中的高中,到年7月高中毕业考进北京大学中文系。 记得,济生小学在府东二路路西,也是善堂办的小学。自然,那善堂就叫济生堂。它的高小,办学质量和水平也是远近有名的。济生小学的两年里,我依旧成绩优异,还是名列前茅。这一点,我同窗11年半的曾宪国可以证明。当然,课余,我依旧在读还珠楼主和张恨水。即使武汉解放,百废待举的新中国,对这些旧小说和他们的作者,政策还是相当宽松的,一般人仍旧可以自由租赁,随便阅读。 读济生五年级时,年5月16日,武汉解放。记得,解放前的几天,汉口沿江大道,白崇禧对码头和趸船实施爆炸。爆炸的巨响和浓烟烈焰给江城带来了惊恐和不安。我们学校也停课了。那些日子,人虽小,我却经历了也见证了我故乡的一个旧时代的结束和一个新时代的开端。 我后来知道了,眼看国民党的失败已成定局之时,他们的华中“剿总”副总司令兼第五绥靖区司令张轸决心率部起义。张轸编组了第一二八军和第一二七军作为起义的基干力量,在高级军官中进行起义的宣传和联络工作,并与中共取得联系。张轸原打算在河南信阳起义,后由于白崇禧将他的部队调到武汉以南而使计划流产。5月上旬,即将成立的中共湖北省委、省人民政府、省军区及各厅局负责人,已经陆续到达汉口北边不远的花园,花园成为湖北省党政军领导机关临时所在地。武汉国民党军这时开始南撤。13日,江汉军区部队的布告张贴到了汉口近郊的岱家山。14日,由于泄密,张轸在武昌被白崇禧扣押。逃脱后,张轸在一二八军军部召开军官会议,决定立即起义,并派人过江到汉口迎接解放军进入武汉。15日下午1时许,国民党华中军政长官公署司令长官白崇禧乘“追云号”飞机逃离武汉。这一天,张轸率部5个师2万余人在武汉附近宣布起义,在贺胜桥西北地区截击白崇禧退却部队,俘获部分人枪。当天晚上,敌武汉警备司令、58军军长鲁道源发表“放弃武汉”书面谈话后,仓惶撤离武汉。16日清晨,白崇禧留在武昌的鲁道源,要晏勋甫去武昌坐火车走,他仍未去,而是发出命令,要汉口警察在16日照常站岗,随后晏勋甫睡去,等他下午三、四时一觉醒来,解放军已经进城了。16日下午2时,四野第师先头部队进入汉口市区,汉口宣告解放。这一天,隐藏在长江上游的渡船,就鸣着胜利的长笛返回汉口,第二天就恢复了轮渡。17日上午,四野第师之一部,从葛店进入武昌市区。同一天,江汉军区独立一旅一万多名指战员从蔡甸出发,解放了汉阳。至此,武汉三镇解放了。19日,汉口公共汽车管理处隐蔽起来的18辆公交车,重新行驶在市区。这一天,早在5月8日奉命停播、准备南撤的汉口广播电台以“汉口人民广播电台”的呼号重新开始播音。22日,武汉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成立。24日,武汉市人民政府成立。25日,新建的中共武汉市委员会成立。江城武汉获得新生。从16日汉口解放开始,一直到二十几号,一个星期内,武汉大街上游行不断。16日那天,解放军上午从江岸和黄陂之间的谌家矶出发进入市区,下午4点进入中山大道,离我们济生小学不远的市一男中的几百名学生,走出校门,汇集到中山大道六渡桥,打着“迎接解放”、“热烈欢迎解放军进城”的横幅和彩色小旗字,抬着学校美术老师叶在树画的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的像,扭着秧歌欢迎子弟兵进城。 武汉一中具有这样一个旧时代的结束和一个新时代的开端的鲜明色彩。 老汉口人称之为“市一男中”的武汉一中,始建于年,先选址在汉口唐家巷,后来搬迁过满春路,还有说曾经在友谊路待过的。年春,市府教育、工部两局,勘定市区西南忍冬街一块平米的空地做新校址,设计施工两年,建成新校舍。时任汉口特别市长,张之洞的儿子张仁蠡,于年4月20日刻有一块石碑,碑文记录了新校舍的建设过程。“忍冬街”后来叫任冬街。实际上,武汉一中的校舍坐落在府东四路和府北一街,也就是解放后改名为前进四路和民主一街交叉处的西北角。 其时,适逢历史风云变幻,社会潮流动荡,“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成了武汉一中师生安身立命的社会追求,“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成了这些爱国的进步的一中人的求学修身的进步校风。一些时代的弄潮儿在这里指点江山激扬文字了。先是年的“一二·九”运动。36届校友密加凡、朱文尧是一中参加运动的主要领导人。著名诗人曾卓(原名曾庆冠)是那一届的学生,也是“一二·九”运动的积极参加者。曾卓后来回忆说:“凭着强烈的爱国热情而投身到大潮中,我只是一个普通的参加者,但以那为起点,决定了我一生的道路。”这应该就是我们一中各位学长的心声,也镌刻下来那个年代武汉一中青年学生成长的轨迹。这些先驱者薪火传承,便是年,一中的“一二·九”运动的中坚人物集合起来组建了民族解放先锋队。抗战胜利后,年,中共南方局负责人董必武派共产党员陈梅影以教师身份到武汉一中领导学生运动。一中学生徐晓峰联合多所学校进步青年组建了一个“武汉学生剧团”,剧团的领导者张孟林就是武汉一中的第一名学生地下党员。年,武汉一中的教师组织了“罢教”、“饿教”和“索薪”的斗争。年,黎明前最黑暗的武汉,一中师生成立了“壁报联合会”、“安全互助委员会”,特别是“新民主主义青年联盟”,引导人们追求解放。那时一中的地下党员还有张师韩老师。 我进一中时,校长还是老校长江家瑞。年,来了新校长张薇之。到我们高中毕业的年,张薇之校长调任武汉工农速成中学校长,继任武汉市教育局副局长。张薇之校长离任后,继任一中校长的李如璞,先以“工作组组长”身份进学校担任党支部书记搞阶级斗争,在“反胡风”、“肃反”和“反右”的乱世里,用他手上的强大的杀伤力给武汉一中带来很大的伤害,那是一阵过眼的云烟,一个“文革”中“工宣队队长”式的人物。危局渡过,直到年,卢世璋老师执掌校长大印,学校生活才回归正道。5年前,年8月10日,武汉一中建校80周年华诞,我应邀代表届老校友返校参与盛会,拿到一本纪念画册《立潮头竞风流赢得满园百花香——武汉市第一中学剪影》,在《领导风采》一页里,解放后到“文革”前的老校长,只有江家瑞、张薇之、卢世璋三位的身影,而没有这位李如璞的任何图文记载,应该就是历史的结论。那一页,是用一中师生的身心伤痛翻过去的。 张薇之校长是我们这一代武汉一中学生终生难忘的好校长。他年在成都金陵大学中文系读书期间就同时在正则会计学校担任应用文的教师了。年投身党的学生运动,成都“双十一”学生运动后被迫离开学校,后来一直以教师的身份从事党的地下工作。他来一中,是带着武汉市军管会的任命书来接管学校的一个举措。治理和发展一中,他对语文教师有一个要求是:“一口话”,就是必须讲普通话;“一支笔”,就是必须写文章;“篇”,就是要写篇文章;没有这三条,你就没有资格当语文课的老师。事实上,他自己就是说得一口京片子漂亮的普通话的。年夏天,我们届高中毕业50周年,校友返校聚会时,薇之老校长还参加了我们的聚会。令人扼腕的是,10年后的年4月1日,我们这一届学生毕业60周年,返校举办“甲子归来聚会感恩”的盛会,薇之老校长已然作古,只能是他长子张政先生带来薇之老校长的著作《教育之树常青》赠送给我们留作纪念了。 当年,一进一中,我们确实见识了不一样的生活。 我们那时候虽然年少,却也曾热血沸腾。 历史业已记载下来,年6月爆发的朝鲜战争,随后由党和政府发出的“抗美援朝”的号召,也在我们武汉一中激发得师生们热情高涨,斗志昂扬。先是“参军、参干”运动。年冬的一次,我还在济生小学,没有赶上。到年上半年的第二次,我在一中了。这一次,我和我们初中一年级的一些同学也响应号召报了名,要投笔从戎,精忠报国。结果,因为年龄不够,没有被批准。这一批,我们有12名同学参加了人民空军。6月间,他们进入沈阳空军第八航校学习飞机无线电技术。有的,后来也开赴朝鲜战场参战了。与此同时,从四川沿江而下到武汉再乘京汉铁路火车北上,而后跨过鸭绿江开赴朝鲜前线作战的,成建制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指战员,中途要在武汉休整,一中也分配有接待住宿的任务。我记得前后大概有四、五批之多。这些志愿军指战员,一律在各班教室打地铺睡觉。一日三餐的饭,他们自己做。这时候,我们学生全部停课,都以班为单位在操场上搭棚子,砌大灶,架大锅,烧小火,炒粳米。我们都学会了将生粳米炒得焦黄,香脆,还酥松可口,一嚼就碎,一碎就能下咽,一下咽就能吃饱肚子。炒好以后,我们会给每个战士的干粮袋填装得满满的,让他们在行军中有充足的“香米饭”可以吃饱肚子。除了填满战士的干粮袋,我们还会装满一个又一个的麻包,顺带,我们也学会了缝麻包的技术。每每这个时候,学校操场上可就是一幅壮观的风景画了。那景致,那氛围,那韵味,真的不亚于电影里农村支前的热闹情景。稍稍偏后一点时间,跟抗美援朝战争有关的活动,就是我们学校还接待了一批前线伤员回国养伤的任务。为此,那一年的寒假放了四周长的时间。虽然接待的伤员不多,任务不算很重,但是,师生们的热情不减,虽然如今我记忆模糊,依稀其间,仍然感人至深。 那两年,配合抗美援朝的爱国主义教育,革命英雄主义教育,武汉一中还不定期地为全校师生组织各种报告会。我至今留有较深印象的是两次。一次是,年5月16日,我初中毕业前夕,为庆祝武汉解放4周年,学校邀请那时候被称为“现代花木兰”的解放军女战士郭俊卿来给我们讲战斗故事。再一次,是请来了被美誉为“中国的保尔·柯察金”的吴运铎作报告。特别是吴运铎这一次。 吴运铎年长我20岁,出生在汉阳蔡甸的一个农民家庭。他父亲是安源煤矿矿上的记帐小职员,很难养活全家,少年吴运铎飘泊在那里做过挑煤工,捡过煤渣。7岁的时候,正值共产党领导的安源煤矿俱乐部为工人谋取福利,他得以进入煤矿东区职工子弟小学就读,参加了儿童团并担任宣传员。由于煤矿上有许多机器设备,他少年时便对机械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打风房中空气压缩机巨大的飞轮让他认识到机器的力量,最大的梦想就是当管机器的工人。年夏天,国民党反动军队开进安源,屠杀革命者,学校停办,吴运铎的家庭生活也陷入绝境。年,他随家人迁到湖北黄石。经父亲的同事介绍,兄弟几人都进矿当了学徒,后来当了电机师傅。为了弄清机器工作的原理,吴运铎在繁重劳动间隙把车间里的一个小阁楼打扫干净,当成了“书房”兼“实验室”,把装机器的破木箱翻过来当书桌,又省吃俭用买来一些工业小丛书,学习机械知识。他还开办了讲座,把机械知识讲给工友们听。全国抗战爆发后,吴运铎不远千里,奔向皖南云岭,年参加新四军,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那以后,他做过新四军司令部修械所车间主任,淮南根据地子弹厂厂长、军工部副部长,华中军工处炮弹厂厂长,等等。在淮南根据地时,他因陋就简,带领职工自制土设备,扩大了枪弹生产。他还主持设计研制成功枪榴筒,参与设计制造37毫米平射炮以及定时、踏火等各种地雷,为提高部队火力做出了贡献。在生产与研制武器弹药中,吴运铎多次负伤,仍以顽强毅力战胜伤残,坚持战斗在生产第一线。他是中国抗日战争时期根据地兵工事业的开拓者。年10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和全国总工会授予他特邀全国劳动模范称号,并将他誉为中国的“保尔·柯察金”。新中国成立后,—年,吴运铎担任中南军政委员会工业部兵工局局长、副局长,所以,那一段时间他都在武汉。武汉一中请他来做报告,应该就是这段时间里的事情。后来,他就在北京俄专留苏预备班学习了。吴运铎最爱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那本书,最敬佩书中的主人公保尔。年冬,中央送他到苏联去治疗眼睛。在莫斯科,《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作者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夫人听到了他的英雄事迹,医院看望他。苏联医生对这位“中国保尔”十分崇敬,经过悉心治疗,吴运铎的部分视力得到恢复,于年回国后应邀参加了天安门国庆观礼。年,他拖着伤残的身体写下了自传体小说《把一切献给党》,发行达余万册,并被翻译成俄、英、日等多种文字,成了那个时代鼓舞人们奋发向上的教科书。他给我们武汉一中的师生作报告时,《把一切献给党》还没有写出来,但是,书中的事迹和精神都十分传神地给我们讲出来了。六十多年过去,我至今不忘的是,吴运铎说:“我们时代的年轻人,虽然不是驴推磨似的打发日子,如果我们今天不比昨天做得更好,也学得更多,生活就会失去意义。”对照《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里保尔·柯察金说的生命的意义是一个意思。保尔·柯察金是说:“人最宝贵的就是生命,生命对于每个人来说只有一次。人的一生应该这样度过:回首往事,他不会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为碌碌无为而羞愧;临终之际,他能够说:‘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解放全人类而斗争。’”这句话,在那个年月,几乎就是我们这一代年轻的读书人的座右铭。我们崇拜保尔·柯察金,也崇拜吴运铎。我是进一中读书半年后的年7月22日加入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请吴运铎来做报告的时候,我不是当时的班长就是团支部书记,记得,我是跟着学校团委的负责人,还有别班的两三个同学一起到武汉市总工会大院里去邀请他的。 这样的崇拜,也许现在的一些年轻人难以理解。那没办法。我们那个时代,就是一个崇拜英雄、追随英雄的时代,真的很难想象现在一些人这么顶礼膜拜演艺界的一些明星。回首往事,我们这一代人绝不后悔。我们至今也坚信不移的是,一个没有英雄的民族,一个不崇拜英雄的民族,甚至于,一个有意无意矮化乃至丑化自己的英雄的民族,真的是一个没有希望没有前途没有未来的民族。 那几年,在新时代的新一中,还有许多事情让我们感受特别深切。比如,我们见证了甚至还在某种意义上参加了解放初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和几乎同时展开的“三反”、“五反”运动。 所谓“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是年秋天到年秋天在中国开展的知识分子的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运动。前后持续时间大约有一年。主要是分清革命和反革命,树立为人民服务的思想。运动由教育界逐步扩展到文艺界和整个知识界。据统计,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全国大约有多万知识分子。广大知识分子爱国热情很高,大多数学有所成的知识分子留在大陆迎接解放,参加国家建设。知识分子学习热情也很高,他们要求了解新社会,了解中国共产党,了解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只是,这些知识分子大多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长期在旧社会受教育,生活,思想上难免留下旧社会的烙印。为帮助他们摆脱剥削阶级世界观的束缚,树立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共产党在知识分子中广泛组织了马列主义基础知识的学习和党的方针政策的学习,以及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和理论的学习,采取各种方式对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教育。比较集中的思想改造学习运动则是从年9月下旬在北京、天津的高等学校教师中首先开始的。9月29日,周恩来受中央委托,向两市高校教师学习会作了《关于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的报告。同年11月3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学校中进行思想改造和组织清理的指示》,要求在学校教职员和高中以上学生中普遍开展学习运动,号召他们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联系实际,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进行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并指出这次运动的目的,主要是分清革命和反革命,树立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此后运动由教育界逐步扩展到文艺界和整个知识界。年秋基本结束。运动中,由于有“组织清理”的内容,一些不能选择家庭出身的来自地主、资本家家庭,或者自己有过一些复杂历史经历的教师,也遭遇过一些过头的做法。年底到年10月和“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几乎同时展开的“三反”、“五反”运动,则明显地带有阶级斗争的色彩。所谓“三反”,是在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中开展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运动;所谓“五反”,是在私营工商业者中开展的“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斗争。先是在年10月开始的增产节约运动中,揭发出大量的贪污浪费现象,于是有了“三反”运动在全国展开。在“三反”运动中,又揭发出资产阶级不法分子同国家机关中的贪污分子密切勾结、从事犯罪活动的严重情况,于是有了“五反”运动。我们这一代人都知道的,大贪污犯原中共石家庄市委副书记刘青山和原中共天津地委书记张子善被判死刑,就是“三反”、“五反”中的典型案件。自然,运动高潮期间,一些地区和单位曾经发生过逼、供、信的现象,误伤了好人,犯了扩大化的错误。 这两场运动里,我们这些学生做了些什么呢?“看守”老师中被隔离审查的“老虎”,并且防止他们“外逃”!记得,当时,学校老师中有复杂历史经历的人,比如李行夫老师,还有总务处经手钱财和物资的职员,都曾经被隔离审查。那隔离的地方,也就相当于“文革”中的“牛棚”吧!今天看来,都算是一种特殊的私设监禁处所、违法剥夺人身自由的做法,当时却是天经地义的革命行为、专政举措。在隔离室“看守”倒还好说,顶多也就是熬夜值班容易犯困。有意思的是,为防止那些被关起来审查的“敌人”外逃。我们被选拔出来的“可靠”的学生,就是团员、班干部之类的吧,三三两两地组成一个个小组,为了不让逃跑的“老虎”认出来,都要化妆,穿着借来的西装,或者长衫,有的还戴着礼帽,加上墨镜,布防在沿江码头,从集家咀一路往下,四官殿、江汉关、粤汉码头,还有大智门火车站,循礼门火车站,居仁门火车站,以及通往黄陂、孝感、黄冈、汉川的长途汽车站,都是堵截、抓捕点。有时候,所谓“形势紧张”之时,一个小组值班,往往还会一夜到天亮。不知道那时候的行路人,看着这帮学生伢们这番打扮,不说奇装异服吧,也会觉得怪怪的,既不是拍电影,又不是玩游戏,他们都在干什么呢?现在回想起来,我们自己也会觉得好笑,可是,在当年,那可是被看成一场严肃的阶级斗争呢!我们可都是站在斗争第一线的小战士呢! 说起英雄崇拜,除了保尔、吴运铎,我们还读魏巍的名篇《谁是最可爱的人》,读《卓娅和舒拉的故事》、《普通一兵》、《绞索架下的报告》、《牛虻》,我们心目中还有刘胡兰、董存瑞、黄继光、邱少云……所有这些,到年参加武汉防汛,都成了引领我们忘我的大无畏精神前行的灯塔和航标,我们的精神支柱。 这样的学习和影响,在年的武汉防汛中得到了一次完美的呈现,接受了一次合格的的检验 武汉俗称江城。浩瀚长江穿越龟、蛇两山滚滚东去,加之龟山之北有汉江汇来,又有东湖和诸多湖泊点缀其间,实属大美河山荟萃之处。小时候我就知道,我这故乡有“东方芝加哥”的美誉。年5月,小女儿子墨和我飞往美国第三大城市芝加哥,和大女儿子犁母、女,并儿子子剑一家会合,参加孙子梦泽的芝加哥大学毕业典礼。典礼结束后,我们有两天游览芝加哥。看芝加哥河也是穿越市区流过,再看连缀在一起的密西根湖烟波浩渺,我就相信武汉和芝加哥确有一比了。我们都知道,汉口在清代属夏口县,当汉水入江之口,原来有大片的湖沼地。清末湖广总督张之洞筑襄河长堤就是汉口背后的张公堤阻水,在长江沿岸又修筑了刘家庙的护江堤,这两条长堤将往昔的湖沼地带围了起来.逐渐成为闹市。因此.汉口的安危,全系于两堤。从地形地貌来说,武汉地处长江中游,“九曲回肠”的荆江河段就在它上游不远之处,加上长江和它最大的支流汉江在此汇合,每当雨季,特别是盛夏酷暑之时,伏汛滚滚到来,常常出现水灾险情。若是两江洪峰同时到来,那夹击的合力,更是让武汉水情险象环生。其中的汉口龙王庙,位于长江和汉江交汇处,河道狭窄,水流湍急,是长江著名险段之一,也是武汉防洪的心腹之患。武昌月亮湾险段,深泓逼岸,堤外无滩,险段冲刷严重,水下岸坡较陡,历来也是武汉市汛期防守的重点。 历史上的年,长江流域发生的特大水灾,淹死十四万余人,其中,两湖灾情最重,号称千湖之省的湖北70个县中就有50个县受灾。整个江汉平原一片汪洋,洪水浸泡时间长达三个月之久。那一年,可以说是武汉历史上的空前大浩劫的一年。历史资料显示,那一年,进7月,武汉三镇连续降雨十多天,长江水位陡涨,市区街道开始出现积水。8月15日,武昌大堤溃决,全城陷入水中,省政府水深2尺,大量民房被淹,20万人无家可归。汉口,大智门火车站前、江汉关、古德寺等地都有较深积水,部分警捕不得不站在邮筒上指挥交通,人们在水浅处用木板临时搭桥,而水深处则只能乘坐舟楫通行。8月下旬,气候炎热,交通瘫痪,食品奇缺,物价飞涨。8月28日、29日,蒋介石乘永绥号军舰由南昌抵汉,巡视武昌、汉口。30日,蒋介石发表《告鄂水灾被难同胞书》,也认为,“此次水灾惨重,为历史上所未有”。遗憾的是,他当还认为,“政府今日唯一急务为救济灾民与清灭赤匪”。直到9月,水势才逐渐退去,水灾造成损失惨重,武汉三镇直接受灾难民五十余万人,据不完全统计,死于洪水、饥饿和瘟疫的有3.26万人。这就是“武汉全镇,竟至覆灭”,“鄂渚之三镇,昔日繁华,顿成泽国”的“空前未闻之大浩劫”,在中国近代史上留下了令人难以忘却的创痛。 到年,武汉又一次面临洪水的巨大威胁了。这一年,汉江水位从3月底就开始上涨,6月初就超过了历史同期最高记录。6月下旬,武汉附近地区连降暴雨,25日武汉关水位突破了26.30米的警戒水位,比年同日高出2米多。这以后,水位继续上涨,市郊大片土地遭渍水淹没,堤防内受渍水,外遭江水浸泡。严重的汛情,直接威胁着武汉的安全。武汉市硚口区所辖堤防,上起邹家街沿襄河经过水厂上街、宗关街、汉水桥、艾家嘴再贯穿一条古老的汉正街、沿江大道至武汉关横堤止,全线长.60米,大部分堤防是根据年水位的设防标准修筑的,设施简陋,地下管道复杂,隐患多。解放后,虽经年年培修,但并未从根本上消除隐患。于是,6月21日,为防范水患,中共武汉市委发出关于加强防汛工作的紧急指示,要求全市党组织立即采取有效措施,做好防汛的一切准备工作。27日,市委和市政府向全市人民发出庄严号召,动员人民起来确保武汉地区国家建设和人民安全。人们从工厂、机关、部队、学校、农村、街道纷纷奔赴堤防前线,开始了一场和洪水的大搏斗。在长江洪水猛涨到历年最高水位28.28公尺的前两天,全市堤防已完成了第一期加高加固工程,堤頂标高达到29公尺半到30公尺。从7月中旬到8月下旬,长江、汉水一个洪峰跟着一个洪峰严重地威胁着武汉市時,武汉市的防汛大軍又先后完成了四期堤防工程。英雄的武汉人民从7月17日到9月13日,和28.28公尺以上的特大洪水,整整相持了58天。8月18日最高的洪峰來到武汉市,長江水位猛涨到29.73公尺,为近百年所罕见。那些天,沿江沿河四级到六级的北风交集着雷雨,浪涛汹涌,但是堤防工程已经跑在洪水前面,像铜墙铁壁般地迫使高出武汉市区地面三公尺到七公尺的滔滔洪水洪水从堤外东流而去。多风的秋季來到之前,漫长的堤线外已经敷设好了三道防浪设备:贴在堤外护坡上的芦席、装石竹笼;挂在堤脚的柳枝、芦柴;堤身三四十公尺以外的防浪木排。防汛战士们先后在堤上抢救了两千多次较大险情,其中八次是形将溃口的大险,保住了堤防安全。据统计,以王任重为总指挥的防汛指挥部,下设10个分指挥部,组织29万人的防汛大军,总计用在堤上的土方万立方米,可以在北京和武汉之间筑成二道半宽高各一公尺的长堤;用了麻袋万条,草包万个,芦席83万张,芦柴高粱杆余万斤,莞箕38万担,用於防浪的木材能绕武汉市75圈。还有大量的火车、汽车、驳船投入。当时,市委、市政府在防汛大军中开展立功活动,全市共评选出防汛功臣名。9月18日,武汉关水位开始回落,10月3日退至警戒线以下。历经多个昼夜的武汉市防汛斗争终于取得了胜利。这是武汉市万人民创造的历史奇迹。 武汉一中的紧急动员大会是在7月12日下午召开的。张薇之校长讲了防汛斗争的形严峻形势,动员师生员工参加防汛,号召共产党员、青年团员和进步青年发挥先锋带头作用,组成青年突击队上前线,投身到抢险和巡堤的战斗中去。在后方的也要努力做好支前工作。动员大会后,我们高一这个年级级,我们高一4班,全都热血沸腾起来,纷纷写决心书,踊跃报名。比我们高的高二同学邓有则还跟他们班的朱兆翔一起连夜创作了一首《动员起来,参见加防汛,保卫大武汉》的歌曲,在《一中生活》上发表出来。过了两天,任务下来了。我们班46个人里,批准了16人组成一个小分队,开赴汉江北岸硚口区罗家墩河堤段,任务是巡堤排查险情,紧急时参加抢险。小分队成员有魏开泰、朱谋溪、鲍厚俊、黄志鹏、汪钺、魏开泰、李开发、何德政和我,等等,由体育教研室潘幼卿老师带队。我们的驻地是江堤内侧的武汉市公安学校。 出发那天,防汛总指挥部命令硚口分指挥部派来军队卡车接我们奔赴前线。开车的时候,我们唱响了当时十分流行的苏联歌曲《共青团员之歌》。歌曲词作者是伽里契,曲作者是谢多伊,中文译者是赵枫。我们唱一遍中文,又唱一遍俄语,一遍又一遍,唱个不停。我们歌声嘹亮,雄壮,慷慨,也带有几分悲壮,充满英雄气概,又满怀勇斗洪水决胜在望的希望。唱到动情是,我看到,不少同学和我一样,两眼都闪亮着晶莹的泪花了。那中文歌词是: 听吧战斗的号角发出警报,穿好军装拿起武器,共青团员们集合起来踏上征途,万众一心保卫国家!我们再见了亲爱的妈妈,请你吻别你的儿子吧!再见吧,妈妈!别难过,莫悲伤,祝福我们一路平安吧!再见了亲爱的故乡,胜利的星会照耀我们,再见吧,妈妈!别难过,莫悲伤,祝福我们一路平安吧!我们自幼所心爱的一切,宁死也不能让给敌人,共青团员们集合起来踏上征途,万众一心保卫国家!我们再见了亲爱的妈妈,请你吻别你的儿子吧!再见吧,妈妈!别难过,莫悲伤,祝福我们一路平安吧!再见了亲爱的故乡,胜利的星会照耀我们,再见吧,妈妈!别难过,莫悲伤,祝福我们一路平安吧! 俄语歌词是: МузыкаВ.Соловьева-СедогоСловаА.ГаличаПротруби?литрубачи?трево?гу. Все?мпофо?рмекбо?юснаряжён, Собира?лсявда?льнююдоро?гу Комсомо?льскийсво?дныйбатальо?н.Досвида?нья,ма?ма,негорю?й, Напроща?ньесы?напоцелу?й; Досвида?нья,ма?ма,негорю?й,негрусти?, Пожела?йнамдо?брогопути?!Проща?й,края?родны?е, Звезда?побе?дынамсвети?. Досвида?нья,ма?ма,негорю?й,негрусти?, Пожела?йнамдо?брогопути?!Всё,что?сде?тствалю?бимихрани?м Никогда?врагу?неотдади?м, Лу?чшесло?жимго?ловувбою?, Защища?яРо?динусвою?.Досвида?нья,ма?ма,негорю?й, Напроща?ньесы?напоцелу?й; Досвида?нья,ма?ма,негорю?й,негрусти?, Пожела?йнамдо?брогопути?!Проща?й,края?родны?е, Звезда?побе?дынамсвети?. Досвида?нья,ма?ма,негорю?й,негрусти?, Пожела?йнамдо?брогопути?!Проща?й,края?родны?е, Звезда?побе?дынамсвети?. Досвида?нья,ма?ма,негорю?й,негрусти?, Пожела?йнамдо?брогопути?! 这是我们这一代年轻人的歌。后来,上北京读书和工作了,我还不止一回唱过。最动情是两回。一回,记得是0年7月,我们中国作家协会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联络委员会的部分同人,陪同当代台湾著名作家、中国统一联盟创盟主席陈映真及夫人,并他的战友、台北《人间》杂志同仁曾健民夫妇、吕正惠夫妇、施善继夫妇等人,游历黄山,两岸文学战线战友商定了《台湾新文学思潮史纲》一书的写作和出版计划,要高举统一大旗对台湾“文学台独”思潮展开全面的系统的深刻的批判,情绪高昂,分别时,在去机场的大巴车上,眼见大家因为就要离别而一派黯然,气氛显得压抑,我提议大家用歌声相互作别,我自己就自告奋勇,先唱了这首《共青团员之歌》。再一回是年4月2日中午,在汉口洞庭街号“小贝壳”餐厅,我们的“甲子归”第二场大活动,初中届和高中届各个小班的餐叙。餐叙的高潮,先是朱谋溪朗诵他为这次聚会创作的诗《我们也曾年轻过——致“甲子归感恩聚”》。过一会儿,游立德唱歌掀起了另一个高潮——全体齐唱前苏联歌曲《共青团员之歌》。当我们的男中音歌唱家缪也上场,征求大家意见时,是我提议唱这支歌的。这是因为,我记得,那时候,在一中,这几乎是“第二校歌”。那年月,我们这一代人,恰同学少年,激情洋溢,唱这首歌的时候,总在豪迈里带有某种悲壮的意味。这回再集合,再唱,这样的意味更为浓郁了。朱谋溪上来指挥,缪也领唱,他用俄语先唱一遍时,在座的很多人也用俄语跟着唱了起来人。随后的中文齐唱,一个个岁在80的老年人,仿佛都回到了青春年华,风华正茂,就像那一年开赴防汛前线时,意气风发,斗志昂扬起来。现场,甚至,随着歌声飞扬,一只只晶莹闪烁的泪眼也飘飞起来点点滴滴的泪花了。 回到年的防汛,我们那时候集合起来踏上征途,万众一心是要战胜洪水,保卫我们美丽的家园大武汉!当时,武汉防汛第一线是由码头工人和别的产业工人为主组成的抢险队,我们高中学生的任务是巡堤,要求是不放过任何险情,当然也不放过任何破坏江堤的坏人。我们16个人加潘老师的建制是一个加强班。在统一划分的一段两公里长的江堤上日夜巡查。4个人一班,每一班三个小时,一天轮两班。潘老师会跟每一班走一趟。我们的具体任务是,发现子堤和母堤的堤面、堤肩、堤坡一直到母堤内堤基两米远的田边小路和草丛里,泥地上,所有的管漏,还有蛇洞和小动物打的洞。再就是江堤外侧有没有滑坡的迹象。白天和晴天还好,夜晚和雨天,这样的巡查是很艰难的。尤其是,风雨交加,倾盆大雨。或者大雷雨的时候,什么雨衣和胶雨靴全都派不上用场,必须穿草鞋、披蓑衣、戴斗笠,一手拄一根粗竹竿或者木头棍子,一手拿一根手电筒,或者提一盏马灯,才能出门上堤。这种日子里巡堤,常常还会摔得一身泥猴似的。尽管这样辛苦,甚至艰难,我们还是发现了不少的险情的。一旦有险情,比如冒出一些水泡的小的疑似管漏,我们都会及时处理,一边用堤上、堤下备用的草袋装填土石方压漏并留守观察。稍大的闲情,我们会晴天吹哨雨天打锣,像古代烽火台那样连接一个个堤段,报警。 有一次,7月下旬的一天,临近傍晚,暴风骤雨中,我们邻近的管段内,只见汉江浊浪滔天,一个个巨浪,冲过了堤外远处的防浪木排,冲散了挂在堤脚的柳枝、芦柴,冲击着贴在护坡上的芦席、装石竹笼,还有码放堆积的装土麻包草袋。连一条条水蛇也惊恐得往堤坡这边争先恐后地急游了过来。听到报警的信号,我们这一班的四个人,还有刚好巡视我们班的潘老师,连忙冲了过去。一看,堤坡上,一排士兵,还有工人抢险队的人,巡堤的学生,二三十个防汛战士,已经手挽着手,站在齐腰深的水里,筑成一道人墙,抵挡那一排排一阵阵的恶浪冲刷了。说时迟,那时快,我们五个人不由分说,全都跳进汉江水里,和人墙边上的战士挽起胳臂来,任他风吹浪打了。不料,不大一会儿,我脚下一滑,出溜了下去,也摔脱了旁边的战友胳臂,竟被一排浊浪卷着离开了人墙。我不会游泳,到现在年至耄耋仍然是一只在长江边上出生又陪伴着长江水长大的“旱鸭子”。一看不好,潘老师迅即游了过来,一把抓住了我的头发,把我带回到岸边来。不去想像可能的后果了,回到驻地开班会,潘老师和同学们表扬我,我在真诚地感谢潘老师的同时,还是检讨了自己没有注意安全防范,比如抓紧身边战友的胳臂等等。 那次抢险后,我发高烧了,记得是39℃吧,同时还拉肚子。结果,我医院医院。医生说,主要是灌了太多的江水,而那江水,是很脏的。我们巡堤的时候,常常看到淹死的猪和牛的尸体,有时候还会有遇难的人的遗体,再加上总有泡烂的房屋建材和竹木家具飘流而过。当然,平时,大家也会有个头疼脑热或者拉个肚子什么的。我们但是住在公安学校,是在教室里睡地铺,酷暑盛夏时节遭遇百年不遇的特大洪水再有“前赴后继”的大雷雨,相当潮湿,闷热,以至于,绝大多数都感染得了一种“奇痒难熬”的怪病“绣球风”,日子过得很不轻松。 不过,住在公安学校,我们也有小小的乐趣。比如,教室门外,我们已经筑起了纵横交错的小小的防水堤,防止水淹我们的“营房”。门对门的教室之间,那原先的走廊里,两道小堤中间,也就人造出一条小河沟来。滂沱大雨过后,竟是一条波涛滚滚的小河。我们常常将武汉人用的竹篾碳篓子,大约一尺半长、一尺宽、一尺深吧,斜一点角度,空篓一面侧身卡放在小河中间抓鱼。通常,夜里睡觉前下篓子,第二天天亮收篓子,一定有收获。当然,我们不吃,也没法吃,防汛前线的伙食质量和水平都很高的。那时全国都支援武汉防汛,像我们经常吃的菜里,香肠炒鸡蛋,香肠炒雪里蕻,原材料都是从上海运过来的。 医院还有一个小小的故事,颇有几分浪漫色彩。我医院之前,我们同年级别的一个班上的何德政同学已经先住过了。何德政是北方人,好像是南下干部子弟,年龄也比我们大点儿,个子挺高,显得早熟。医院里有位护士叫冯婉球,是广西壮族姑娘,也就十九、二十吧,有一天值夜班,突然向我打听何德政的情况,而且问得非常详细,还要我谈谈对他的印象。等我出院回到公安学校驻地一问,何德政还非常坦率地承认,他跟冯婉球姑娘谈恋爱了。大家都笑话他,说他在演奏战地浪漫曲呢!可我,隐隐地觉得,何德政是单恋,那位壮族护士姑娘好像并不喜欢他,比方说何德政不爱干净,总显得脏兮兮的,等等。防汛结束后,她还去过我家,说她跟何德政没有来往了。 日子一天天过去,武汉防汛第天的时候,我们都“复员”回到了学校。武汉防汛总指挥部在全市评选防汛功臣时,我们班的朱谋溪、鲍厚俊和我,都被评定为“武汉防汛三等功臣”。我们班,还有一位评为二等功臣。他就是魏开泰。 魏开泰还被追认为武汉防汛烈士。他是在防汛前线罹患急性痢疾高烧不退倒下的。他为保卫我们的大武汉奉献了自己年轻的生命!我们的魏开泰同学,永垂不朽! 我进一中读初中的时候,春季班是四个班,我在2班。读高中,我们年级七个班,我在4班。有意思的是,高中一年级录取时,《长江日报》发榜,在全部录取的名新生里,我总分排名第6。这已经是一个不错的排序了,可我总还是觉得不太舒服。没考第一,怎么连个二、三也不是呢? 在一中的五年半,几乎每读一个年级都换一位班主任老师,不像现在这样班主任通常都会把一个班带到毕业。我印象深的是初一和高一的胡文毅老师,初二的吴连芝老师,初三的杨菊英老师,高三的许樊新老师。 胡文毅老师是我接触的第一位一中老师。她出身湖南湘潭一个世家。她说齐白石早年是她家一名雕花木匠。她自己,在北京师范大学读到地理学硕士研究生的学历和学位。在一中,她教地理,初中教自然地理,高中教经济地理。年高考的时候,地理考卷上有一道题是,从北京到昆明怎么走?如果能说出不同的路线更好。那时候,我们这些中学生谁都没有旅行的经历,我就是凭着文毅恩师传授的知识,圆满地回答了这道考题的。而且,全卷,我得了95分的高分。听文毅恩师的地理课,还引发了我读徐霞客的兴趣。文毅恩师告诉我们,徐霞客是江苏江阴人,明朝末期科学家、地理学家、探险家,旅行家和文学家。他从22岁新婚那年开始,一直到去世前一年止,长达33年的岁月里,矢志不渝地从事旅游考察,足迹遍及了我国19个省。进入云南丽江时,因足疾无法行走了,仍坚持编写《游记》和《山志》,基本完成了多万字的《徐霞客游记》。年55岁时,云南地方官用车船送徐霞客回江阴。第二年正月,徐霞客病逝于家中。徐霞客的生前友好钱谦益称赞他是“千古奇人”,以他的游记和日记整理成的《徐霞客游记》是“千古第一奇书”。著名的世界科学史家李约瑟博士认为,这部书对地理学的贡献甚至达到了西方地理学的现代水平。《徐霞客游记》中对各地名胜古迹、风土人情,都有记载,开辟了地理学上系统观察自然、描述自然的新方向;既是系统考察祖国地貌地质的地理名著,又是描绘华夏风景资源的旅游巨篇,还是文字优美的文学佳作,在国内外具有深远的影响。《徐霞客游记》得以成书和流传至今,是非常不容易的事,它经过了一系列曲折坎坷的道路,许多人为了这部书的流传和出版,作出了可贵的贡献,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徐霞客去世后不久,钱谦益写信给徐霞客的族兄仲昭说:“霞客先生游览诸记,此世间真文字、大文字、奇文字,不当令泯灭不传,仁兄当急为编次,谋得好事者授梓,不惟霞客精神不磨,天壤间亦不可无此书也。”后来钱氏又写信给刻书家毛子晋,希望他将游记“仅存数本”刻印出版,广为流通。历经历史上的天灾人祸,《徐霞客游记》流传下来实属不易。文毅恩师在课下特别跟我说:“你喜欢文学,作文也写得好,将来长大了,你也要去旅行,也要写游记。”她把她自己的一本年商务印书馆的《万有文库》本《徐霞客游记》送给了我。还在一次我们远足即郊游东湖,路过她住家的武昌珞珈山口外武珞路边文华中学时,在教师宿舍她家,吃了她下厨煮的鸡蛋挂面之后,领我到她和她丈夫著名画家端木先生的书房,品鉴了他收藏的丁文江主持整理的《徐霞客游记》问世以来最完善的版本,那是年商务版的16开大字本的一版。我这些年,一直都热衷于旅行,除了国内一些名山大川,世界上一些国家,还在75岁时去了南极,76岁时去了北极,还打算接着再走,不能不说有我文毅恩师的读万卷书还要行万里路的启蒙教育的作用。我喜欢把自己叫作“一个背着行囊走在路上的人”。当然,除了随手写一点游记,比如5年写的《到托尔斯泰庄园朝圣》等等,甚至还创作了文学作品《南极风情画》,等时间和精力集中了,我还会写作《航行欧洲两海》、《探访南北两极》等等。 文毅恩师留给我难忘的记忆,还有严辞训斥了我两回。 一回是,在初一2班,我是班长。有一次星期天,我和五个同学结伴过江远足到东湖,早上去的时候天气很好,下午回来风云突变。我们那时候远足,全凭两条腿步行,从武昌江边的中华门码头走了一个珞珈山、东湖的来回路程,全都是十三、四、五岁的小男孩儿,用现在话说都累得要趴下了。下午五点的样子,等我们再回到中华门码头一看,都傻眼了。乌云密布的天空低垂,好像一朵朵黑云就要从天上掉下来的样子,江面上雾濛濛一片,阵阵大风吹得浑黄的江水翻滚着一排排的白浪。武汉长江两岸照例“封江”,轮渡已经停航。怎么办?有同学提议,他家有个亲戚,是表姐,在不远处的彭刘杨路武汉第一护士学校当老师,他要带我们去找她,求她帮忙,把我们安顿在教室里过一夜,第二天再回汉口。我不赞成。那时没有手机,没有
|
当前位置: 汉川市 >武汉一中是我成长的文化大摇篮上曾庆
时间:2021/3/30来源:本站原创作者:佚名
------分隔线----------------------------
- 上一篇文章: 校友湛娜我与汉川一中
- 下一篇文章: 没有了